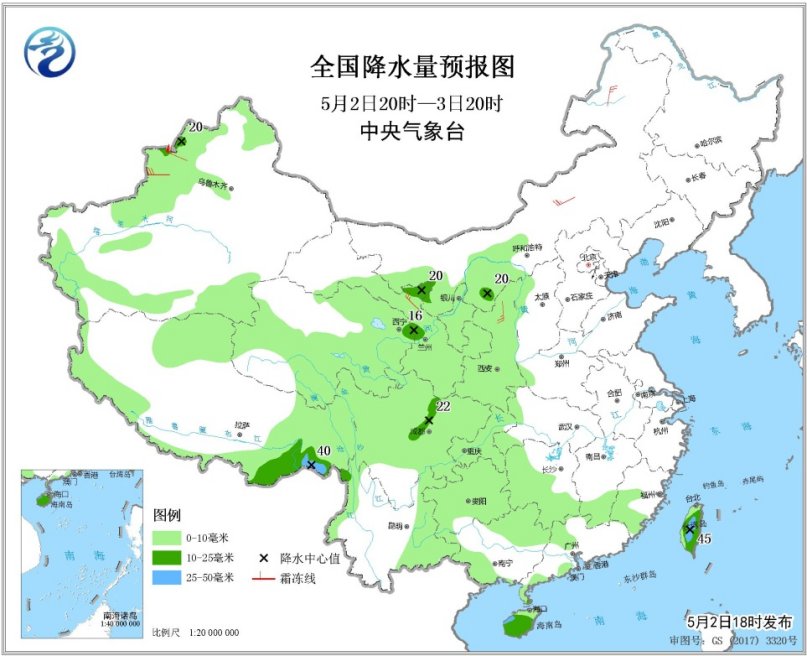近年来民谣音乐的这一波高烧,发端于2013年,选秀节目《快乐男声》的参赛者左立翻唱了一首《董小姐》,使得这首歌连同原唱者宋冬野一起红遍大江南北;2015年,《中国好声音》的参赛者张磊又在电视上演唱了马頔的《南山南》,进一步地延续了民谣音乐在娱乐市场中的火爆;与此同时,好妹妹、陈粒等乐队与音乐人也在这一波风潮中各自闯出了一片天地;2017年2月,民谣音乐人赵雷作为补位歌手,登上了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歌手》,以一曲自创的《成都》走红于大众的视野。赵雷的走红,也正好成为近几年中国流行音乐市场中,民谣这个音乐类型持续高烧的顶峰。当然,如果说赵雷红的比上述几位晚,那自然有失公允。2014年1月,在以原创歌曲为主打产品的《中国好歌曲》上,赵雷就已经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亮过相了。不仅如此,在节目当中,评委刘欢老师还盛赞了赵雷的原创曲目《画》,称其为“到目前为止见到的最漂亮的一首歌词”。自此之后,赵雷的歌手生涯也走进了迅速上升的阶段,直至参加《歌手》节目时爆炸性的走红,其名气与影响力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先于他成名的宋冬野与马頔。

歌唱家朱逢博
然而民谣音乐进入中国广大听众的耳朵,并不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计划地向中国大陆的音乐家提供台湾通俗音乐的资料,随后,著名歌唱家朱逢博便翻唱了《橄榄树》、《小茉莉》等台湾校园民谣歌曲。在那个音乐生产尚未市场化的年代,体制内音乐家对台湾民谣音乐的引入,成为民谣音乐进入中国大陆的开端。

老狼
90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流行音乐的生产也渐渐脱离了歌舞团、文工团等系统。1994年,香港的大地唱片公司在北京推出了合辑《校园民谣1》,成为大陆民谣音乐流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在合辑中献声的老狼、丁薇等民谣歌手,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同一时期,在校园民谣这种颇具书卷气质的音乐类型之外,一种更加世俗、贴近寻常百姓生活的都市民谣也兴盛起来,其代表人物便是李春波与艾敬(而这两位歌手也曾分别是海政文工团与东方歌舞团的演员)。时间来到新的千年,虽然民谣音乐一度在主流的音乐市场中不再流行,但随着越来越多新兴的音乐展演、发行渠道的诞生,诸如周云蓬或左小祖咒这样的独立(或曰地下)民谣音乐人也各自拥有一批属于自己的忠实听众。直到近几年,民谣一词再度成为国内流行乐坛的热门话题。
80、90年代民谣在今天的复现
一位民谣歌手可以在流行乐坛走红绝非偶然,这不仅是民谣这种音乐类型的功劳,也需要歌手本身具有过硬的业务水平,更少不了唱片公司和媒体的产业力量推波助澜。尤其在流行音乐市场异常纷繁复杂的当下,来自欧美、日韩的新潮作品不断冲击着国内听众的耳朵,香港、台湾的流行歌曲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就算在本土出品的音乐作品里,赵雷的民谣歌曲都还不是最时髦的类型。但赵雷的走红,恰恰是因为民谣这种音乐类型具有简单、通俗的特性。无论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水平有没有提高,当下国人的生活节奏肯定是越来越快了。配合着这种节奏,近年来的国内音乐市场上出现了一批随着韩流一起来袭的电子舞曲,形式上与电视节目《盖世音雄》里出现的差不多,无论是流行歌曲、摇滚还是说唱,只要加上些电子音乐的元素,再经一众韩版小鲜肉们(无论是韩国原装的还是国产出口转内销的)的演唱,就离走红不太远了。又或是仿照日本少女偶像团体建立起来的许多国产的少女偶像团体,无论歌唱的好不好,颜值够高就能红,甚至颜值差强人意也没关系,最起码还能占个人多势众。然而,三手的通俗EDM(如果说欧美是将电子舞曲流行化的起点,日韩作为娱乐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也先于中国引进了这种音乐形式的话)和青春肉体攻势也无法全面覆盖整个流行音乐市场,或者换句话讲,大剂量的感官刺激也不是人人时时都能接受的。民谣音乐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市场上,便刚好为吃腻了进口快餐与本土杂烩的流行乐迷递上了一盘儿清口的小点心。

李春波

艾敬
民谣,或者准确的说是当代民谣(与各民族的传统民歌相区别)这种音乐类型,确实以其简单、通俗的音乐形式容易让大众所接受。当改革开放初期,曾因为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喜儿伴唱而走红的朱逢博,唱起轻松而又平易近人的民谣音乐时,听惯了过去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注重宏大叙事的革命歌曲的广大听众,便迅速为自己找到了休闲娱乐的新宠。当然,这一时期朱逢博的声音也同样受到了钟情于《白毛女》那种“字正腔圆”唱法的听众的质疑,认为这些通俗的“新”歌有些“不够严肃”甚至“矫揉造作”。而作为90年代初通俗音乐去政治化与市场化浪潮的产物,这个阶段民谣歌曲的主题便更加聚焦在个人情感的抒发上了。老狼、高晓松等人口中纯真浪漫的校园生活,让多少青少年辗转反侧,一时间,草地、吉他与恋爱成了各大专院校中的日常景观。而在校园民谣之外,都市民谣也给广大听众带来了不一样的信息。比如在李春波红遍大江南北的金曲《一封家书》中,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爸爸每天都上班吗,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这样的歌词,着实挑战了以“为革命献身”为主旋律的主流话语;而艾敬的《我的1997》也通过第一人称的直白叙事,表达了对于“午夜场”、“八佰伴的衣服”的向往,对繁荣的物质生活的歌颂也不再是禁忌了。我们不禁感叹,每一波流行音乐的风潮确实都紧跟着时代的脉搏。在改革开放与市场化的早期阶段,流行的民谣作品中对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体现了一种对“自由”的朴素呼唤,而80、90年代民谣音乐与音乐人的形象也因此固着下来了。
对于一个职业音乐人来说,归纳与吸收既有音乐作品中的优质元素,再经由自身的加工而创作出新的作品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专业技能之一,今日当红的赵雷身上那种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气质就是显而易见的。自不必说赵雷自己就写了一首名叫“八十年代的歌”的歌,又在其中唱着“我的耳旁还回荡着那一首八十年代的歌”;在赵雷的另一首知名歌曲《未给姐姐递出的信》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在音乐形式与题材上对于郁冬的《北京的冬天》和张楚的《姐姐》的复现。对于曾在80、90年代引起轰动的民谣音乐中的成功元素的使用成为当下再度流行的民谣音乐中的一大特点,甚至在赵雷的外形上,我们都很容易察觉到一种错置的年代感——当2014年赵雷登上《中国好歌曲》的舞台时,他那一套整身的牛仔服、立起的领子和吉他不正是某种齐秦或是老狼经典形象的再现吗?于是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当赵雷出现在“六十年代生人”的刘欢老师面前时的那种一拍即合了。有人曾开玩笑地评论说“故乡”、“火车”、“穷”和“得不到的爱情”是时下这一批民谣音乐人主要歌颂的题材,不过回看过去,这老几样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如果说“艳粉街”和“小芳”是二十年前那一代人集体的故乡和情人的话,那么今天的“鼓楼”和“董小姐”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过,即便是新瓶装旧酒,我们仍然不得不佩服,时代的文化工业总是能在浩如烟海的音乐市场上为自己找到投资标的。正如二十多年前,香港的刘卓辉与台湾的张培仁把大地和魔岩开到了北京,挖掘出老狼、高晓松或是“魔岩三杰”这样优秀的音乐人,开启了大陆流行音乐的一段神话;在宋冬野、马頔和赵雷的背后,也有像摩登天空与Street Voice这样成熟的音乐厂牌作为支撑。一位歌手可以从流行音乐市场里杀出重围,自身的努力自不必说,而围绕着歌手本人,制作、发行、推广等一系列专业而又繁复的工作同样必不可少。以赵雷为例,2014年10月,赵雷第一次登上上海简单生活节时,台下便已聚集了许多独立音乐的听众;2016年3月16日,一档现场音乐类网络节目《大事发声》第一次上线时,赵雷也出现在了首期的表演嘉宾名单中(与他同期表演的另外一位歌手是影响力远在其之上的伍佰);同年10月,当赵雷再次回到简单生活节表演时,他已经取代前两届的徐佳莹与张震岳,成为“街声舞台”的压轴歌手了。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便能发现简单生活节与《大事发声》的幕后操盘者,正是赵雷所签约的唱片公司Street Voice。当代的音乐产业,业务范围比起二十年前大了许多,唱片公司包装与推广艺人的渠道也不仅仅是传统的平面媒体与电台、电视台。自2008年起,户外音乐节在中国的爆炸式发展让音乐人可以更直接地与听众面对面交流,定期去音乐节转转也被包装成了流行音乐消费者的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比起从台湾引进的简单生活节,长期扎根国内市场的摩登天空与草莓两个音乐节品牌(同属摩登天空公司旗下)更是早已成为了小众音乐人走进主流视野的良好平台。而在互联网+的时代,实体唱片不再是听众欣赏音乐作品的唯一途径,通过与腾讯合作推出的《大事发声》节目与自身所拥有的数字发行品牌Packer派歌,Street Voice成功地占领了在线流媒体视听的高地,走在了音乐网际传播的时代前列。由此看来,信息高速路上的“董小姐”又岂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村丫儿小芳能媲美的?

赵雷
背后的隐忧:
小情小爱抽空了民谣这一音乐类型的进步性
然而,即使民谣红了,赵雷也红了,近几年流行起来的这一波民谣风潮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无论是宋冬野,还是马頔,当下都市民谣中的小情小爱实在过于泛滥了,赵雷也是如此。只要简单回顾一下赵雷的作品,《阿刁》也好,《孤独》也罢,这种描写无望爱情或自说自话的歌曲比比皆是;亦或是近日在《歌手》节目上演唱的《三十岁的女人》,踩到了许多女性网友的底线,不仅小情小爱,简直透露出保守的气息;而在2014年发表的《理想》中,一句“理想今年你几岁”简直让人分辨不出赵雷与病毒式营销金曲《老男孩》的区别。
小情小爱是否就是民谣音乐唯一的主题呢?只要我们回看民谣音乐的发展历程便可知道绝非如此,当代民谣这种音乐类型的体量所能承载的绝不仅仅是如此轻薄短小的个人情怀。当20世纪60、70年代,当代民谣席卷欧美乐坛的时候,以Bob Dylan、Joan Baez等人为代表的民谣歌手所关注的反倒是社会正义与公共议题,诗意的歌词书写与平易近人的音乐表达成为了传播进步社会观念的武器。在我们的邻国日本与韩国,冷战铁幕另一端的冈林信康与金敏基等民谣歌手也积极地投入各自国内的社会运动,创作了大量反映底层人民生活处境,控诉社会不公的民谣歌曲。而在宝岛台湾,70年代的民歌运动中,李双泽与杨祖珺等人创作的民谣歌曲,更是反抗国民党统治与压迫的呐喊。公共性与社会关怀从一开始就没有在民谣这种音乐形式中缺席。在80、90年代的台湾与大陆乐坛,民谣音乐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关怀也并不罕见。罗大佑早期的民谣作品与张楚的歌曲虽然具有各自强烈的个人风格,叙事手法上也多以个人叙事为主,但个人叙事中蕴含着对社会与公共生活的思考和批判,不仅在美学表现上,更在思想深度上甩了近些年流行起来的都市民谣好远。
倘若上述例子稍有厚古薄今、厚远薄近之嫌的话,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当下仍然活跃的独立民谣音乐场景,投向那些也许并不为广大流行音乐听众所熟知的歌手身上,我们仍然不难发现,当代的中国民谣歌手中不乏持续关注社会问题与公共生活的创作者。取材于社会现实,当歌手深沉而又悲怆地唱着《中国孩子》,或略带戏谑地调侃着“买房子”与“黄金粥”的荒诞时,我们健忘的大脑难道不会被调动起来吗?麻木的神经难道不会再次敏感起来吗?精致的语言与优美的旋律在他们的音乐中从来没有缺席过,但这样的民谣音乐可以带给听众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娱乐消遣而已。当歌手用“小小事件”来诉说让全国人民都震惊的毒奶粉事件时,我们便不能仅以前卫或者古怪来形容这个音乐人了。兼具美学追求与社会关怀的民谣歌手在当代的所谓独立民谣场景中并不罕见,只是尚未成为产业的宠儿。
小情小爱与自说自话绝非民谣音乐的极限,即便个人情感的表达是文艺作品亘古不变的创作主题之一。倘若近年来走红的民谣歌手无法突破自怨自艾的创作局限,视野里仍然只有鬼打墙式的情爱与无所指涉的“理想”的话,纵使市场可以创造出良好的机遇,音乐作品本身的生命力也会因为内容的苍白而日渐衰微。与此同时,对于在这一波热潮中培养起来的民谣听众来说,也容易错失通过聆听音乐来引发社会思考的机会。当然,这并非一种不可避免的遗憾。当代的中国社会,早已过了那个把《武训传》当毒草一样批判的年代了;描写才子佳人的文艺作品也不会再被当做靡靡之音而只能让人偷偷摸摸地传播了。只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可以不再把“游遍世界”当做理想,除非他一心要当个现代的麦哲伦;而“北京的冬天”这样的题材,不仅20多年前的郁冬写过,前几年海峡对岸的陈绮贞老师也写过,犹如对于成都、厦门、西藏这样的旅游目的地浅尝辄止的介绍也还是适可而止的好。行万里路的确需要勇气,也必定有其内涵,但如果民谣歌曲中这样的主题一再重复,那时间久了听众自然会找不到旅行的意义。
作为近年来独立音乐人走进主流视野的成功案例,赵雷与宋冬野等人的走红建立在个人的努力与文化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之上;但作为已经迈入而立之年的,成熟的音乐创作者,“无法长大”并不能作为小鼻子小眼睛的挡箭牌。当代的中国并不缺乏“巨婴”,希望年轻一代的民谣歌手可以走出小情小爱的桎梏,让新一代的民谣爱好者不留遗憾。
大视窗
新闻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