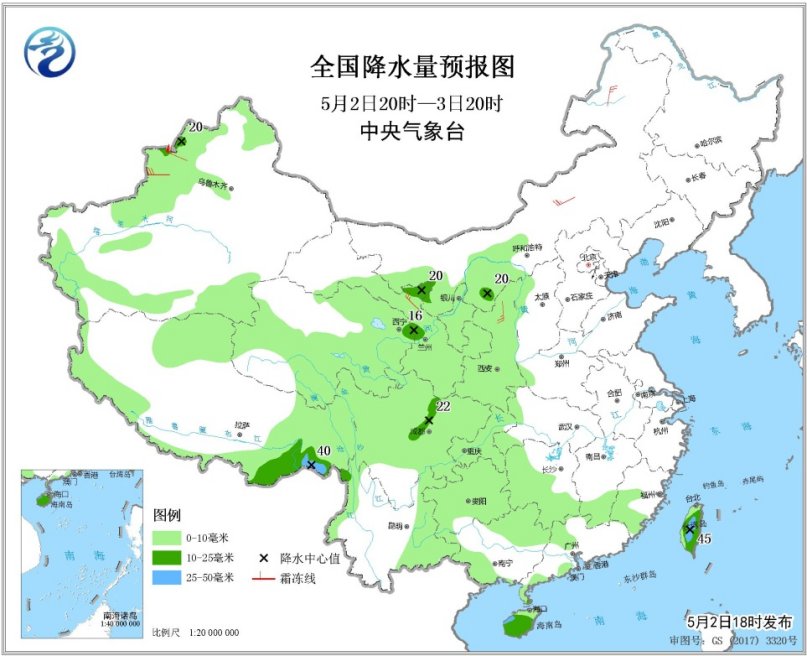编者按:今年是“达达主义”百年。在尚未经历过达达主义运动的现代中国,达达也并非不存在。但具有中国特色的“达达行动”距离遥远西方达达主义运动的兴起,实际已经迟到了60余年,如同往平静的水面扔下一颗石子,涟漪层层向外荡漾开来,最后的余波才抵达了中国。

1986年11月23日厦门达达“焚烧事件”现场, 厦门新艺术广场
在尚未经历过全面系统的达达主义运动的现代中国,达达也并非不存在。在一些当代艺术家身上,你还是能看到这群诞生于100年前的“颠覆分子”的影子。“85美术”新潮的艺术家,他们在展厅里孵蛋,卖虾,洗脚,他们把《中国绘画史》和《现代艺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作一堆,他们“袭击美术馆”等等等等,但是他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达达行动”距离遥远西方达达主义运动的兴起,实际已经迟到了60余年,如同往平静的水面扔下一颗石子,涟漪层层向外荡漾开来,持续60多年,最后的余波才抵达了中国。

黄永砯
在上1980年代的那场新潮运动中,“厦门达达”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黄永砯是将它推入中国艺术史的核心人物。他们“怀疑”、“警惕”、“否定”,与“达达”反对一切,包括反对自己如出一辙。“1983年到1986年三年的时间,国内的现代艺术运动,包括青年艺术群体和展览可以说是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现代派’已经从瘟疫一样令人害怕变成一种赶时髦的口头禅。尽管其中并没有什么足于称道的或可以留史的艺术杰作出现,只有各种折衷,夹生,粗糙和充满模仿痕迹。但是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切使得艺术界的阵脚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同时造就了新一代人。这种混乱和参与制造混乱本身就具有价值,这是一个明显的‘达达’意味,在中国明确地提出‘达达’精神的时代看来已经到来。” 黄永砯在1986年曾经这样写道。
但是随着“85美术新潮”的悄然落幕,“厦门达达”的成员也纷纷各奔东西,依然在践行“达达精神”的也就黄永砯一人,他却在多年后坦言,不会再提起达达,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身在巴黎的他,得知《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记者的采访内容是关于达达,礼貌回复了一次之后便如石沉大海。虽然他说过达达已死,但他也同时说:“达达是永远不死的。死的东西是永远不死的,我们说不死的才是死的,两个矛盾性的东西要保住,这不是因人而异的问题,是因时而异的问题。”
每一代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机会和舞台由达达主义起始,艺术创作开始使用现成品,有了借用、挪用和戏仿的特征,使艺术创作之途从此由一条大道,而有了分岔的小径。众多从事装置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们都深受达达的影响,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

大尾象工作组(合照) 左起:陈绍雄,林一林,徐坦,梁钜辉
在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大尾象工作组”,这个暗示“四不像”的艺术组织由艺术家陈劭雄、梁钜辉、林一林和徐坦组成。
1991-1996年期间,大尾象在新型商业城市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宫、酒吧、大厦地下层和户外等临时空间,自主组织策划了五次展览;作品借用了西方艺术语言的表达方式,包括:装置,行为,录像,摄影,网络和绘画等。主题内容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爆炸型起飞,广州率先出现的诸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如:人口迁徙,文化危机,以及城市环境急剧变化等。在1990年代他们以单薄的力量与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对峙,独具勇气。
相比较1980年代,“厦门达达”直接采用了“达达”的名称,“大尾象”成员之一林一林则认为,真正到了的1990年代,达达主义创始人马塞尔·杜尚的故事和谈话录早就被消化了一遍,他们其实更关注当时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学生时代,确实受过大量来自“达达”的熏陶,而1990年代,直接的影响已很难说还在发生。“我个人很喜欢杜尚的艺术,态度、智慧都很佩服,不像早年绘画性的大师,学生时期对那种会关心,我对杜尚的热爱会超过毕加索和达利。”“大尾象”的重要成员陈劭雄前不久去世,以“孵蛋”行为艺术闻名的张念也因病去世,中国当代艺术先锋们的记忆正在渐渐沉入历史。

陈劭雄,耗电七十二个半小时,1992,日光灯, 电表,木架,雨衣
那时不少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于马塞尔·杜尚都充满了崇敬与神往,达达主义发端于1916年,其实直到1960年代后西方才认可杜尚的艺术地位。在林一林眼里,杜尚就是一个“信使”(借用最近西方的说法),把达达的精神概念跨越几十年传递到中国。
85新潮时,林一林也参与了“南方艺术家沙龙”,做“沙龙”的时候他还在读美院,而作为个人的表达是在1990年代开始,自己的创作在展览中呈现。1990年左右, 85新潮时期锋芒毕露的艺术家很多都出国了,剩下来的艺术家大多对社会失望。当时的林一林和陈劭雄,在“南方艺术沙龙”做完之后有一阵子不知道做什么好,毕业了几年虽然在分配的单位,但是还是想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环境也不好,在广州也没几个真正做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很难说和达达有直接正面的关系,我们整天面临生存压力和作品发表的限制,所受物质条件的限制,比如没有展厅办展,是很具体的和难以解决的问题。那段困难太实在了,需要解决很多和艺术表达没有关系的问题。”物质方面受到不充裕的限制,但个人在艺术方面表达反而觉得非常自由,只是做作品“不自由”,这样的不自由就是说在国内没有当代艺术系统的支持,当时只有官方的系统。
1991年初开始做“大尾象”的展览,便计划每年做一次大的展览,到了1993年因为没有找到展览场地,只能在大街上做。到了1994年,已经做了三年了,其实每一届都想找批评家策展人一起合作,这一年就找了侯瀚如。“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存在的问题,是艺术家和评论家所关注的更多是在画面直接流露对社会的关心和自我情绪的宣泄, 当然这可以表现, 但不是唯一的。 另外一种艺术家, 就是考虑艺术问题的艺术家往往受到忽略, 并不是说这种艺术家没有反映这个社会,而是他们的方式更内在,不那么一目了然。1991年在北京的西三环文献展,我们送去的几张作品照片都预示着我们的作品和八十年代已经很不一样了。”
不可否认,8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对于西方的模仿的痕迹是大规模的,在大氛围下,艺术家会不太在乎个人语言、艺术语言本身的思考,“中国年轻的艺术家比较粗糙地,且很有激情地把西方现代派过滤了一遍,虽然并非每样事情都尝试过。而到了90年代,艺术活动变得更地下,更少人关注,不像85新潮有很多批评家参与写文章,同时还有一些艺术刊物。1990年代初一切变得冷清,参与的人突然间变得少了,回到一个很自然的状态,新一代艺术家开始慢慢做艺术。他们用比较平静的心态对待艺术的问题,从一个艺术上下文去考虑问题,而不是完全现代主义运动激情的方式,并对生存的环境在自己艺术里的有所反映,因为对西方的了解更深入细致,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过滤之后,情绪上是不一样的。” 林一林回忆起1990年代时的冷清情景,同时也记起了当时的艺术家慢慢意识到艺术市场的问题。“虽然当时中国没什么艺术市场,有一些艺术家可以卖一点东西,有批评家认为,这个市场可以取代85的热情,存在让中国当代艺术合法化的可能性。” 很多艺术家包括到现在都在面对生存压力,解决怎么过得更好的问题。其实当时真正不管自己的前景去做艺术的,就是极少数的几个艺术家。
无论理论家们旁观者们如何阐释,在林一林的心里,达达运动,超现实主义运动,影响了更早的85的一代人,也影响到了他们这代人。50后60后的这些艺术家同样经历过“文革”,便不会觉得“运动”离自己很远,他们将达达视为“艺术运动”,“而这种感觉在当时85的那批年轻艺术家身上是反映很充分的。”
20年前,杜尚无处不在,85新潮和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不同程度都受过达达的影响,没有谁比谁更先进。每一代所受的教育,每一代人所经历的事,以及社会文化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都不尽相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机会和舞台,无法用高下分之。“是历史和时间选择了艺术家,而不是艺术家创造了什么。”林一林说。
所有人都是达达的受益者中国当代艺术以85艺术新潮为标志,可以说达达主义对85新潮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与年代有关,第一届大学生都是油画系的,内心深处是印象派,到了85新潮以后便是超现实主义,模仿西方流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所以,说‘中国有和没有过达达都是成立的’。”中山大学教授杨小彦在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采访时说。
“所有这些借鉴达达精神的东西,我们不能把他们称作达达,这是中国特色的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借鉴和发展,和达达的本意没什么太大关系。达达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只有精神层面的意义,任何在视觉方面的借鉴和理论上面的照抄、挪用都是无意义的,只是在内在精神上的借鉴。”尽管在谈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心里挺矛盾的”,但是独立策展人、艺术评论家李旭仍然认为:“现在看到的达达大部分是狗尾续貂,打着达达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反达达,最可宝贵的精神是被商业化了。像禅宗的公案一样,不立文字的。至少在我看到的所谓的杜尚之后的达达,全部都是伪达达,没人是真达达。”确实,经历过85,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且现在仍然活跃的艺术家林一林也说过类似的话:“其实,现在的艺术状况是非常反达达的,非常迎合体制和商业的力量。”
然而,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中前进。“一、达达是不可重复的,它是个悖论,去纪念重复发扬达达,都是违反达达本意的。达达反博物馆、反美术馆、反美术史、反永恒价值的,如果有所谓的‘后达达’‘新达达’都是假的。从艺术史的本意来说,达达的本意并非如此,马塞尔·杜尚在晚年访谈录里就明确表示过这个意思——像把一团垃圾扔到一个很正经的人的脸上去,没想到这些人把这包垃圾精致地包装了一下供在美术馆里了。这事儿他觉得很悲哀。”李旭说。

“厦门达达”拖走美术馆计划草图,1989
艺术史学者马琳对杜尚颇有研究,她回忆起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 “厦门达达”曾经实施过的一次“袭击美术馆事件”,也就是“发生在福建美术展览馆内的事件展览”。他们向福州的美术馆递交了一个虚假的计划,在展览前突然改变计划,动员全体参展艺术家把美术馆外的建筑废料,旧货如水泥模块、砖、瓦、门框、破沙发、条木、旧桌、铁栅栏、下水道管、陶缸……搬入美术馆散置成“展品”,埋头苦干,大干加巧干忙乎了几天。这次行动的结果,当然是在拍完照片以后、展览开幕之前被封闭了,黄永砯说:“我们要袭击的不是观众,也不是美术馆,而是参观者对 ‘艺术’的看法。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空手而来,最后空手而归”。“体现了一种反叛破坏精神,达达在他们思想方面的深刻影响。”马琳说。
不可否认的是,达达的诞生造成了一个艺术史的分叉,达达之前的艺术史是一个统一的艺术史,美学价值是原创,无论是图像原创还是别的技术,都和手工劳动和美术学院体系有关,但是达达之后,不强调原创,强调借用挪用戏仿颠覆,“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原初的原始的美学一直在延续,就是博物馆里的,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自生自灭的,随时生随时死,包括观念艺术。”李旭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达达影响没有中断过,随处可见。“中国当代艺术就是脱胎于西方当代艺术的基本观念,游戏规则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没有人不受过达达影响,他们享受了达达的理论空间和理论基础,否则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不成立的。所有的人都是达达的受益者。”就像林一林说的,厦门达达、大尾象,中国当代艺术里人们愿意承认的那部分,留下的痕迹肯定有,而究竟怎样的痕迹,描述起来,“又实在是太文学性了”。
- 构筑西北绿色屏障07-20
- 同心掬得满庭芳07-20
- “苦甲之地”西海固的蜕变07-20
- 探美新宁夏07-20
- 脱贫硬骨头怎么“啃” 听听基层代表怎么说07-19
- 乡村“蝶变”——且看今日西海固07-12
- 塞上大地花儿美——宁夏奋进60年之文化建设09-02
- 西藏4个非遗项目参加第七届全国非遗联展06-12
- 西藏申报国家级非遗保护专项资金超2000万06-12
大视窗
新闻热点